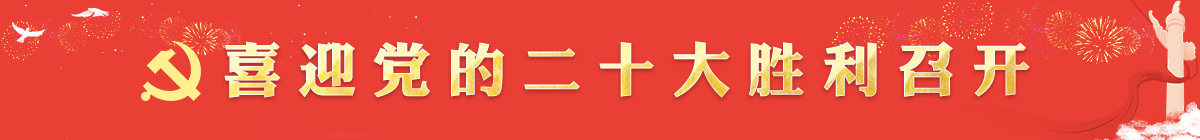本文认为数字女权主义的政治投资是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即Angela McRobbie所说的“消灭女权主义”(“undoing of feminism”)的环境下进行的。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选择、赋权和个人主义的话语使女权主义既是第二性的,也是非必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描述了一系列近期的女权主义抗议行动,它们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重塑了女权主义”(“redoing feminism”)。重塑的关键在于最近的抗议行动如何消解历史和当代女权主义话语里的中心矛盾;更重要的是,关注当地经历的身体政治与跨地域、跨国表达的女权主义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数字女权主义既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压迫性,也体现了新主体性和新社会形态的可能性,本研究最终想要引起人们对这种模凌两可处境的关注。
导言
2014年5月,推特上以“YesAllWomen”为标签的帖子掀起了一股新浪潮,这场运动引起了人们对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厌女症和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的关注。用户们在上面发布关于歧视、骚扰和恐惧的个人故事,强调“是的,所有女性”都遭受性暴力。在德国,女权主义者在#YesAllWomen上发表了有关性歧视和暴力的文章,其中还包括#Aufschrei(强烈抗议)等标签,这在两个地方性抗议活动之间建立了跨国数字联系。#YesAllWomen和#Aufschrei展示了数字平台如何为个体故事和集体模式发生互动提供机会;两者还说明了当地经验的身体政治与女权主义行动(其有效性取决于跨地域和跨国的表达)之间有着重要的互动关系。这些行动揭示了性暴力的普遍性和结构性,并将个别女性的具体当地故事与更大的不平等叙述联系起来。这些行动利用数字化技术来显示全球范围内的性别压迫现象,并将女权主义的抗议运动跨越国界地联系起来,这体现了当今数字化女权行动主义的核心。
数字化平台具有广阔的潜力,它可以广泛传播女权主义思想、塑造关于性别和性别歧视的新讨论方式、连接不同的选民,以及允许出现新颖的抗议方式。标签女权主义(hashtag feminism)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在二十一世纪,数字媒体空间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和全球各地的行动主义形式,进而在线上与线下共同地影响着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学者将数字女权行动主义描述为传统女权政治模式的偏离,认为它带来了许多新的时刻或转折点。首先,它不仅在公共领域培养了讨论女权议题的意识,而且在女权主义内部推动了新的动态参与。其次,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空间,女权主义者可以学习到为什么女权主义者认为无害的东西可能对他人有害或者是令人反感的。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知道交叉性,但并非所有人都知道交叉性压迫的每一种方式(Fredrika Thelandersson 2014,529),而数字平台可以实现新型的交叉对话。最后,数字女性主义的抗议活动与女性身体的相互作用,为新兴的女性主义政治提供了挑衅和冒险的空间,这种政治空间不再强调通过传统法律和立法渠道来追求的平等和权利。也就是说,数字行动主义构成了女权主义抗议文化内的范式转变。
然而,数字女权主义的具体政治投资却很少,这个现象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霸权一同出现。数字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许多问题:数字抗议在被采纳的同时是否也被消耗掉了,而这似乎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必然结果?女权主义者能否团结起来,尽管是(或甚至“因为是”)在“有毒”的网络空间环境中(Thelandersson 2014)?数字女性主义的“微造反”会导致结构性变化吗(这种“微造反”往往与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性和自我企业家形式相结合)(Salime 2014,16)?我们如何理解数字媒体空间空间和街头抗议活动中女性身体政治功能的变化?最后,在容忍不平等、财富再分配固化已成为常态、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越来越难以想象的时代,我们用什么方法衡量政治行动的有效性?
为了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些临时性的答案,本文考察了源自数字平台和行动主义结合的的新女权政治,并将利用这三个案例研究来解释数字女权主义如何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重塑女权主义。
文献回顾(一):女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个人选择的霸权话语与赋权、自由、自尊、个人责任等话语合谋,使得女权主义看来像是第二天性,或是非必需的。这在西方尤其如此。在西方,人们越来越多地将结构性不平等视为可以通过个人成就来解决的个人问题。Angela McRobbie在她的《女权主义的后果》(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一书中描述了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会发生“消灭女权主义”运动,即否认女权主义是必要的,同时又赋予女性“一种名义上的平等形式(具体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并且,消费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参与取代了重塑女性主义政治所必须提供的东西”(2009,2)。Rosalind Gill认为,在当代媒体文化中,“女权主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也被否定”(2007,271),这引发了有关女权政治如何能够形成适当回应的质疑。
McRobbie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学术上的女权主义在回应关于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和代表性主张的争议中自我瓦解,这使得新自由主义中的女权主义的消亡变得更加复杂。正如她所强调的,这种瓦解有着理论层面的原因,如女权主义理论对女性内部差异和身体处境的质疑、身份的消除作为政治基础,以及关于女权主义者代表性的问题(McRobbie 2009,8)。然而,正如Chandra Talpade Mohanty(2013)所论证的那样,这种女权主义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与新自由主义知识文化中激进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批判的主流化趋于一致。即女权主义理论不再与激进主义或“解放”的知识生产有关,而是作为一种商品和学术资本主义声望的象征,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大学在修辞上对性别公正的承诺。
最终,女权主义在学术和大众话语层面消亡,伴随着其他新自由主义倾向——自上而下再分配的社会运动和集体政治的瓦解、不平等现象的扩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被视作能分配财富和民主的有效中立力量。在新自由主义中盛行的私有化和个性化话语将“系统性的抵抗转变为商品化的私人反叛”(Mohanty 2013,968),消解了反叛和反霸权的女权主义政治。
“不稳定性”(precarity,指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这个概念的出现,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当下的“双重纠葛”,并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一种潜在的反叙述。“双重纠葛”是指,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一种对少数群体产生不利影响的永久性不安全状况,另一方面,个人选择、灵活性和流动性等新自由主义话语为打破规范角色和侵蚀传统社会结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一个向上流动、政治和社会平等的幻想破灭的时代,“不稳定”已成为关键的情感结构(Berlant 2011)。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发现自己面临着矛盾的社会角色要求。不同的规范思想会相互竞争。例如,女人必须像男人一样工作(平等就业),但同时如果需要的话,必须始终能够成为女人。因此,在劳动分工、家庭政治和广告中,传统的角色观念依旧不变(Woltersdorff 2011,173)。
这种“不稳定性”也预示着变革的可能性。当女性处境变得更加岌岌可危时(如2008年经济危机后),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以新一轮的出版物、抗议和干预行动做出回应。并且,更重要的是,流行女权主义(popfeminism,又即波普女权主义)与数字平台的兴起相伴而生。数字平台的运用帮助带动了关于女权主义的广泛公开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女性主义的发展与性别歧视是同时发生的。此外,线上和线下空间的衔接对于建立有效的女权主义抗议模式也至关重要。
文献回顾(二):身体政治和女权行动主义
不稳定的女性身体是当代女性主义跨国行动的特征。SlutWalk提倡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穿/不穿,并鼓励参与者穿上适度的着装或裸露着参加抗议活动,但它因展示衣着暴露的身体而声名狼藉。被标签为“极端主义”的FeMen将裸露的胸部视作反抗的象征。
Butler认为:“性别和性是通过身体暴露给他人的,它们被牵涉到社会进程中,被文化规范所铭记,且其社会意义会被理解”(Butler 2004b,20)。正如她所说的,“要发生政治,就必须出现身体”(Judith Butler 2011,n.p.),因为“身体暗示着死亡、脆弱、行动中介;身体始终具有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一种社会现象,我的身体是我的,又不是我的”(Butler 2004b,21)。巴特勒强调了支配性别的规范的双重性质,既是约束又是机会,即“身体是可以以多种方式来占据、超越、改造规范的”(2004b,217)。这些观点对女权行动派起到指导作用。
SlutWalk、FeMen 和 Pussy Riot 这一类女权抗议活动利用女性身体,呼吁人们关注社会性别规范,它们占用这些规范并旨在重新标志它们。这些抗议活动象征性地与以下现象交战:媒体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禁止女性在公共场所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妇女遭受的性暴力。这个过程中,它们揭露了女性身体的“不稳定性”,即女性身体既处于压迫性政权中的不安全状态,同时也是矛盾和潜在反抗的场所。
虽然女性身体一直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关键,但在新自由主义和数字文化的背景下,女权身体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叠性变化。在身份与社会地位脱节的背景下,身体成为新自由主义中身份的主要来源(Rosalind Gill & Christina Scharf 2011,8; Phipps 2014)。新自由主义话语强调身体是通过自我塑造、个人进步和个人选择来实现赋权的场所,但同时也需要对它进行不断的监视、调控和规训。
数字平台同样具有双重功能,它一方面是赋权和身份形成的场所,另一方面是被监控和自我监控的场所(尤其是对女性而言)(Tanja Carstensen 2014;Mia Consalvo & Susanna Paasonen 2002;Tamara Shepherd 2014)。尽管网络女权主义者强调了数字文化具有克服性别二元的潜在可能,但社交媒体平台对商品化自我呈现的强调和物质身体图像的数字传播,使得霸权女性气质更受追捧(即符合传统异性/恋审美的白人女性想象)。即使是今天包含大量在线互动的文本交流,也彰显着这种“自相矛盾的技术文化”,它仍然怀有“将身体抛在身后”的愿望,但与此同时,它却不断地被“幽灵的化身”所困扰,即性别会被关联到一个二分性的身体,不管它是否可见(Niels Van Doorn, Sally Wyatt, & Liesbet Van Zoonen 2012, 434) 。
案例
案例一:SlutWalk,FEMEN,Muslima Pride
SlutWalk于2011年起源于多伦多,因为这之前一名城市警察评论道,妇女应“避免像荡妇一样打扮”,以防止性侵犯。全球范围内的SlutWalk行动引起了人们对强奸文化、荡妇羞辱、受害者有罪论和知情同意的关注。尽管组织者强调SlutWalks没有着装要求,但游行活动因一些女权主义者试图通过在各种脱衣状态下进行丰富多彩的表演来取缔Slut这个词而臭名昭著。SlutWalk以Riot Grrl运动的女权主义美学为基础,大声、愤怒、公开地表达了对父权制的愤怒。与此同时,关于“SlutWalk”策略的重要跨国女权主义讨论基本上在数字空间中发生。
(译注:SlutWalk与种族、阶级、性、宗教等议题交汇诞生了各种复杂实践,如Muslima Pride,其共同目标是反对霸权女性气质。这个过程中,数字媒体使得女权行动经验得以跨国传播。整个具体发展过程详见于完整文章。)
案例二:The “Free Pussy Riot!”Video by Peaches
2012年8月8日,酷儿表演艺术家和音乐家Peaches为她的歌曲“Free Pussy Riot!”拍摄了一段视频。数百人通过社交网站进行了回应,并穿着受Pussy Riot启发的装备(包括霓虹色的balaclavas)在Prenzlauer Berg聚集。在视频中,各种体型和身材的人一起跳舞、跳跃和旋转,在他们的头上挥舞着拳头。与FeMen对裸体的策略性运用形成对比的是,在这里种族和性别等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被面具和制服所掩盖,呼应了Pussy Riot为了集体团结的形象而对个人主义进行象征性模糊的目标,并强调了他们对霸权女性主义的驳斥。
然而,该视频还包括大量未戴面具的人的镜头。许多图片通过淫秽的手势、裸露的身体部位和特写的皮肤来突出身体,特写的皮肤上刻着Pussy Riot的字样。Peaches视频的这些方面,与Pussy Riot创造人物角色来表达观念的想法相矛盾;相反,Peaches的视频是要重新将“Pussy Riot”的发动目标与个人身体联系起来。
正如Carrie Smith-Prei所论证的那样,波普女权主义将“话语和嬉戏的少女气息”与流行媒体的元素结合在一起,以便进行对女性的身体风格化,从而作为一种表演式反抗。女性对自己身体和性的满足和控制是最重要的。而Peaches的视频正是强调:新自由主义中女性身体既是一个承载着霸权女性气质的场所,又是一个自我风格化和性愉悦的DIY空间。Peaches还延伸性地对全球资本主义中的艺术商品化进行了激进的批评。数字广播的视频和歌曲最终创造了一个狂欢和愉快的空间,而女权主义被重新标志为一个创造性地反对性别从属的集体运动。
案例三:#Aufschrei and #YesAllWomen
在历史上,跨国女权抗议运动起源于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此处讨论的抗议活动都与此历史轨迹有关。在#Aufschrei和#YesAllWomen的案例中,Twitter作为数字平台对于建构跨地区和跨国的歧视和暴力事件框架至关重要(这些事件发生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其目的是让人们看到女性普遍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
#Aufschrei运动始于2013年1月,当时德国女性开始在Twitter(https://twitter.com/hashtag/aufschrei)上播报日常性别歧视的个人故事。#Aufschrei还对德国发生的一系列国家政治事件做出了回应。#Aufschrei是德国第一场社交媒体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公众共鸣,推动了对当今德国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的讨论。
#YesAllWomen的出现也是对美国当地事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枪击惨案)的回应。22岁的Elot Rodger开启杀戮狂欢并开枪自杀之前,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个反女权主义者的视频,他在视频中表示打算惩罚拒绝与他发生性行为的女性。在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内,超过100万个帖子使用了#YesAllWomen;这些推文共同强调了今天的厌女症普遍存在,呼吁人们注意性骚扰和强奸文化所造成的个人创伤,以及社会不平等和构成(支持暴力对待女性的)男性特权的结构成因。#notAllMen对#YesAllWomen提出了反对意见,女性主义者为此普及了女性主义普遍性原则。此外,有色人种女性发起“YesALLWhiteWomen”的运动,批评许多帖子中体现出固有的白人特权,并强调在反对性暴力的行动中,有必要关注交叉性。不过,这些运动并不仅仅是重提旧的女权主义争论,而是积极地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重塑女权主义政治。
正如Thrift(2014,1)所说:“#YesAllWomen主题标签坚持对‘例外论’(Exceptionalism)的反叙述,坚持认为这些悲剧是性别压迫体系的表现。”当个人的压迫故事被用一个主题标签汇编时,结构性不平等的集体经历被展现出来,标签女权主义凸显了个人与集体的相互作用。并且,#Aufschrei和#YesAllWomen也特别展露了女性身体既屈从又反抗的矛盾。
结论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Mohanty问道,“当政治(政治的集体公共领域)被简化为个人的时候,‘个人即政治’这一关键的女权主义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2013,971)。我在这里所考察的抗议活动,尽管它们的策略在质量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但它们都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与新自由主义对个人政治的削弱进行了斗争:揭露掩盖差异的女权主义策略普遍化的趋势;关注个人经验与结构性不平等的关系;强调女性个体在公共空间中的持续的不稳定性。这为重新建立一个团结的女权主义政治奠定了基础。
女性身体的不稳定性已经成为当代女权主义抗议运动的争议焦点。对于许多女权主义批评家来说,像“SlutWalk”和“FeMen”这样的抗议运动,运用了一种似乎是在复制(而不是抵制)父权规范的身体政治学。Theresa O’keefe指出,“因为它们不寻求破坏构成’理想’女性身体的实质”(2014,11),“再加上没有对针对女性的暴力、女性的性化、以及女性的身体继续成为种族主义和父权资本主义的战场等问题的结构性描述”,因此,“这些类型的身体政治是危险的”(2014,15-16)。她批评了这些抗议活动使得性暴力和女性身体的性化普遍化。
假设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女权主义者可以继续参与二十世纪类型的社会运动,如像第二波女权运动一样在集体争取社会进步的大环境下要求个人自由,那么最近的这类女权主义者抗议就会被认为是“失败”的(在颠覆、模仿,或嘲笑主流代表或反对父权制方面)。也就是说,它们被认为没有致力于社会关系的根本转变。
然而,在缺乏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品的情况下,以及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个体化和私有化的背景下,行动者只能将集体反抗改造为商品化的私人微观反抗,这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女权主义政治的必要尝试。因此,在这里考察的女权主义抗议应当被理解为基于过程的政治行动。这些行动不是参与社会进步或解放的叙述,而是强调寻找新的政治范式、语言和符号以对抗新自由主义对个人政治的消解的过程。他们对女性主义进行了有争议的重塑,将女性“不稳定”的身体展开来呈现当代社会现实的矛盾。
来源:社论前沿,https://mp.weixin.qq.com/s/ErvFECqOIh9XgefJVjqbcw 发表时间:2028年3月31日